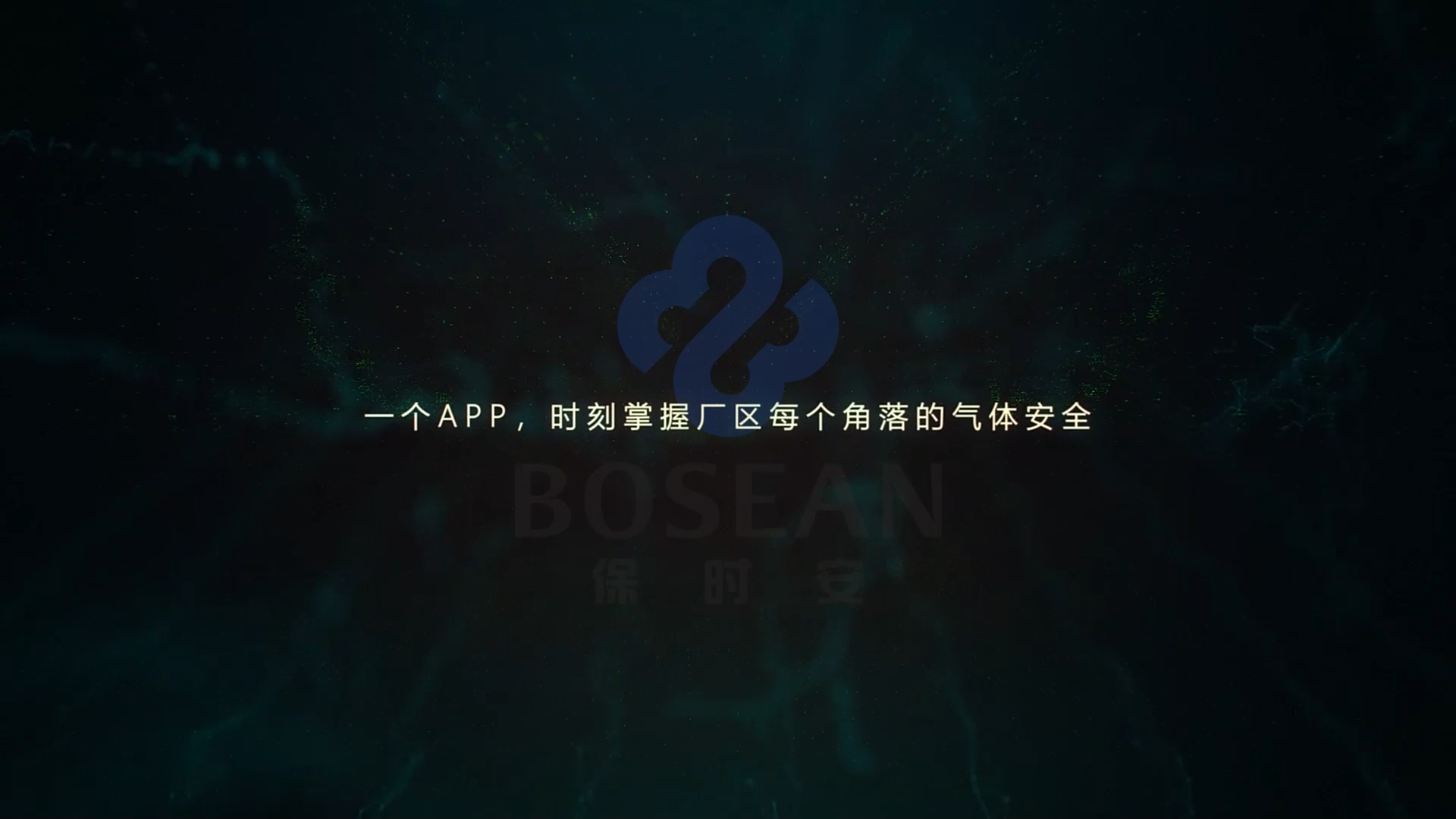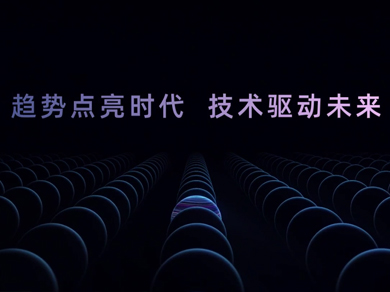执法检查发现,消防法的法律精神和法律条文还没有得到完全落实,“大火巨灾”“小火亡人”“新领域新业态火灾”隐患依然存在,消防安全形势依然严峻。
典型领域:消防设施建设。全国仍有907个县(市、区)和开发区尚未组建消防救援站,全国城市消防站缺建40%以上,市政消火栓欠账率近15%。农村地区公共消防基础设施欠账更为严重。山西“十三五”规划全省应建消防站259个,实建208个,缺建51个,缺建率20%。四川目前尚有67个县级行政区划和开发区没有建立消防救援站。内蒙古按照《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》,全区应建消防救援站302个,目前仅建成148个。
二是新兴风险和挑战。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业态不断衍生新风险,电动自行车、新能源汽车,氢能、光伏、锂电等储能设施,天然气泄漏和大型仓储物流场所等火灾爆炸事故呈增长态势。
一是责任落实不到位与部门协作不顺畅并存
1.地方政府领导责任。个别地方新发展理念树得不牢,统筹发展与安全有差距,对消防工作重视不够、投入不足,公共消防设施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。在产业规划、招商引资、项目建设中审核把关不严,放松消防安全要求。政府消防议事协调机构不健全,有的未建立消防安全委员会或联席会议制度,有的没有实体化运转,协调指导、工作督办作用发挥不明显。消防工作考评激励机制不完善,推动消防安全责任落实的效果有待提升。
3.部门监管协调联动。国家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后,消防救援机构和公安、住建等部门的职责边界不够清晰,监管合力有待加强。
二是住房和城乡建设。专业建设工程的消防审验和工程管理协调机制有待完善,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对消防技术服务、单位建筑的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关系和管理权限不够明确。
城市和乡村消防工作基础不同,法律实施面临的挑战不同,但在基层消防治理等方面存在相近相通的问题。
2.农村。消防法第30条明确加强农村消防工作,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。当前,农村公共消防服务供给不足,消防力量薄弱,建筑耐火等级低、消防基础设施标准低,特别是农村自建房缺少必要的消防设施、防火间距不足,火灾发生频率较高。部分历史文化名村的消防设施严重不足。2016年至2020年,农村地区发生火灾占比从45.6%升至51.7%。今年截至10月,农村发生火灾30.5万起,占总数的54.4%,远高于城镇。
3.基层。乡镇街道的职能部门和村委会、居委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。部分乡镇街道未设置专门的消防职能部门,部分乡镇街道消防安全委员会形同虚设,一些小单位小场所存在失控漏管现象。消防法第32条要求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。部分村委会、居委会没有将群众性消防纳入工作任务,未全面履行防火安全检查和消防宣传教育、建立志愿消防队等职责。个别地区基层消防安全网格组织弱化、虚化,存在“虚挂空转”现象,尚未有机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,火灾防控“最后一公里”有待完全打通。
三是消防意识薄弱与消防知识缺乏并存
1.突出表现。在随机抽查和实地暗访中发现的问题,主要集中在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上。例如:部分单位存在安全出口处安装电子锁、疏散通道上设置障碍物、防火卷帘下方设置障碍物、安全出口的门不能正常开启、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对自动消防设施操作不熟悉等问题。
3.消防知识。公民消防安全常识知晓率总体偏低,普遍不会使用灭火器具,不会扑救初起火灾,对逃生自救技能运用比较生疏。消防法第17条规定,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。目前,社会单位对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投入不足,应急演练不多,参与人数较少。主要防火责任人缺少处置初起火灾的知识和技能,消防安全培训简单化,宣传工作不到位、不扎实。部分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会使用灭火器、不会引导疏散逃生。
消防法第3章“消防组织”和第4章“灭火救援”,重点对消防救援队伍进行了规范,明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、专职消防队应当充分发挥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专业力量的骨干作用,明确加强消防技术人才培养。当前,消防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增强。
2.职业保障亟待加强。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身份属性、抚恤优待、退出机制等有待完善,职业吸引力不强。专职消防员普遍存在待遇保障力度不足、职业认同感低、职业发展空间受限、人员流失量大等问题,特别是一些地方采用劳务派遣等方式招用专职消防员,导致“同工不同酬”,招不来、留不住、更替频繁等问题。2020年,国家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计划招录消防干部3000名,实际招录852名,计划完成率仅26.7%。去年,青海开展了首批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工作,按计划招满的424人中,目前已陆续退出99人,占招录计划的23.3%。